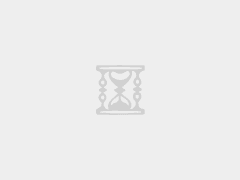20250911,周四,多云
#全民健康信息场#
学习前辈的人生经验
口述历史 | 李舜伟:跟病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
李舜伟,上海人,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1936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镇,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3—1986年赴美国进修,主要研究领域为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药理学。1991—1997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神经科工作数十年,善于诊断和处理临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头痛、失眠等的诊治。2002年牵头筹建北京协和医院心理生理疾病诊治中心,为促进精神心理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书籍5本,参编书籍18本,译著2本。1990年出版的《意识障碍的分类与分级》在一氧化碳中毒国家标准中被引用,获卫生部优秀国家标准二等奖。
曾任法国神经科学会荣誉会员,美国生物精神科协会通讯会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组成员,原卫生部医疗事故鉴定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2011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王:您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李:我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上海读的。中学时我对数理化很感兴趣,学得也很好,所以填的志愿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这种理工科大学。结果报上去以后,老师说你肺里面有一个钙化灶,学理工科太累了,可能坚持不住,让考虑换志愿。这一下子把我弄懵了,我就拿着报名单回家跟我爸商量。我爸说我们家没有医生,要不学医吧,可是我对医一窍不通,他说那就努力努力吧,我就把志愿改掉了。
当时我中学的生物学老师对我非常重视,他觉得我是可以学得很好的,就教我如何在一个月里把三个学期的生物学“灌”进去。我当时拼命啃啊啃啊,总算啃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医疗系。
刚开始我不愿意学医,所以第一学期什么都没学好。但是没办法,爸爸让学,我也只能咬着牙坚持。刚上大学时正好碰到院系调整,所有的课程、科目、讲课方法都要学苏联那套,跟上医原来英美那套完全不一样。但必须扭过来,否则我们毕不了业。第一个学期我学得简直糟糕透顶,到了三年级以后,我突然对学医产生点兴趣了,就比较努力地去学、去记,后来功课就慢慢好起来了,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了。到五年级时,按照苏联标准,我10门课全A,只有一门是A-,我们班上120多个学生,只有3个人跟我一样。所以总算弯道超车超得还可以,最后比较顺利地毕业了。
那时从上海到北京火车是28个小时,要坐一天一夜。等下了火车,我们16个同学一看,就一个字“土”。为什么呢?我们当时是坐到前门客站,从火车上下来,有一帮人来接站。我们一看,这些人戴着西瓜皮帽子、穿着大褂,大褂外面还套着一件衣服。那个时候没有十大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什么的,全都是空地或两排小树,跟上海完全不一样。
当时我们坐着协和派的车到了医院,之后人事处把我分配到内科,我说好,也无所谓。过两天人事处的处长来问我,李舜伟你能不能跟你同学换个位置,你有个同学想学内分泌,你本来被分在内分泌,能不能换出来学神经科?我说我学什么都可以,而且我在上医的时候参加过神经科的科研小组,所以对神经科还是有点兴趣的。就这样我们两个对调了,我就干神经科了。
第一,当时北京协和医院是自己发电的,就现在洗衣房那个位置原来是个发电厂。当时发的电是110V直流电,中国是220V的交流电,所以当时协和发电和美国是一样的。第二,协和有8口深水井,当时工作人员会把水提出来,自己分析水样,消毒后供全院使用。第三,协和有自己的煤气罐,两个大煤气罐就在西门外,当时是直接从开滦煤矿运无烟煤到协和的。所以协和的水、电、煤气都是自己的,不得不说还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我到美国去学习,住的地方跟协和没有什么差别,说明协和早就已经发展在前面了。
还有个例子,协和大门上的门钩都是自动化的。你打开以后手一松,“哒”它自己就缓缓合上了。这个东西是用美国进口的黄铜做的,很贵,现在都没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小偷偷走卖掉了。
病房有一个孩子老发烧,许大夫让我用低温疗法【3】治疗这个病人。我正好之前在上医实习时学过这种方法,管了这个病人三个月,病人状态挺好。许大夫很满意,就建议把我升为代理主治医师。可惜那时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就算了。
当时有一个清朝末年的御医施今墨【4】来讲课,我就跟在他屁股后头抄方子。他看我很卖力,抄得很仔细,就说,小伙子要不要学点东西?我说当然好了。他就教我“对对方”,就是学习一对一对的方子。比如赤芍、白芍一对,桃仁、红花一对,他说你把它们记住,将来你开方子一开就是两个药,而且主治方向都一致,就很好了。我真的记住了,后来在农村里面开的方子还很有效。这些老中医都挺谦虚谨慎的,而且不排斥西医,像施今墨就从不干预西医治疗,他就按照他的理论配合开方子治疗。
后来中医班学完以后要考试,我最后考得很好。我觉得学中医对我有一定的好处,我并不完全靠中医或西医来治病,而是两个结合起来,有时候效果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中医有优点也有缺点,比如一味中药可能能把一个病人治好,但是这一味中药能不能把100个同样症状的病人都治好,那是一个问题,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循证医学。所以国外的人为什么对我们中医有看法,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可能缺乏大数据依据。所以中西医结合之路很遥远,但是应该说是有前途的。因为中药里面确实有些东西有效,比如用麻黄滴鼻子,鼻子就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医要在研究这方面下大功夫,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当时精神科在我们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安定医院算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精神科医院了,所以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怎么诊断、辨别精神科病人的表现等等。
王:在这之后您又去了西藏阿里援藏,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李:当时号召业务好、有本事的人要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就打听什么地方最艰苦,当然就是西藏,尤其是跟印度、尼泊尔交界的阿里,那个地方过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我就跟我爱人商量,她同意我去,我就报名了。那个时候郎景和【11】、张振寰【12】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一拍即合,1973年就一块儿去阿里待了一年。
去阿里跟在上海和北京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讲一下。衣,当时阿里的人一辈子就一件衣服。小孩儿一生下来,他妈妈就用羊毛缝一个小棉袄给他穿。长大一点就补一块,再长大再补一块。所以他们没有里、外衣服的分别,就一件衣服一直贴身穿着。食,就两样东西,酥油茶和糌粑。酥油茶就是把茶放在桶里,再放一块酥油,也就是牛油,然后就开始在桶里敲打,直到打成卤泥汤一样时,就可以喝了。糌粑就是青稞,他们用手捏巴捏巴,捏出一边圆、一边尖的形状,就直接吃。这么吃有好处,在西藏如果吃我们日常的饭,吃完后1小时肚子就饿了,但是吃酥油茶加糌粑,吃完一个上午都没问题,骑马怎么颠都不饿。住,就是帐篷,不要看蒙古和新疆的帐篷,那是高级帐篷,西藏的帐篷,尤其阿里的帐篷就是用牦牛绳打一个结,窟窿很大。半夜三更风吹起来了,外面十级风,里头至少五级以上,男女老少住在一个帐篷里都冷得不得了。行,就是走路和骑马,骑马是必须要学会的。他们给我挑了一匹非常温顺的白马,我一跳就上去了,叫它停就停下来了,很稳当。
王:在西藏有没有难忘的病例?
李:我第一天到西藏就碰到一个18岁的小姑娘,麻疹后肺炎发高烧,42度,这个病很凶的。我们要给她治疗,她不肯,我就跟她爸爸妈妈商量,要打青霉素降温消炎。结果她爸爸妈妈说西藏女孩子不让人家看屁股,我说我是要给她打针治病的。后来我们用了两个钟头,总算把她爸妈和她本人说服了。我贡献了一块毛巾给她清洁消毒,然后打了一针青霉素,打完已经夜里10点钟了,我们就在旁边的帐篷里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去看那个姑娘,结果帐篷里没人了,我害怕极了。结果她爸爸说小姑娘到对面山上放羊去了。我们请她回来量体温,38度,人家已经无所谓放羊去了。
还有一次,一个重病的老先生被拉来找我们,他一进来,房间里就充斥着一股臭味。我们过去检查,发现他右胳膊被羊皮包着,一层层拆开羊皮后,胳膊上全是肥肥的蛆,有几百只了,老人家的整个胳膊都没有肉了,全是蛆。我和张振寰当了那么多年大夫,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蛆,吓得够呛。我们赶紧戴上手套,把蛆一把一把捋到桶里,慢慢地,筋膜和骨头就露出来了。老先生一试体温,40度高烧。我们赶紧用消毒药利凡诺尔【13】给他洗胳膊,洗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用纱布把胳膊缠好。因为人发烧得吃点好的补一补,但是老人家里牛奶、羊奶都没有,我们就让他在我们这住下了。一个月以后,老人家胳膊上的肉慢慢长出来了,两个多月以后,他可以起床慢慢活动了。我们特别开心,这是到西藏以后见到的一个非常极致的病例,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后来我们就问老先生是怎么发生这种情况的,他说一开始有蚊子咬了他的胳膊,他就拿唾液在伤口上面抹,结果伤口越来越大,后来苍蝇什么的就全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真的没法说。
现在已经很好啦,我听说援藏的队员都能吃住在拉萨的医院里了,很不错了。
这个跟文化观念、历史条件不同有关,跟医学方面常识不同也有关系。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在这儿学一套美国做法,回去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就坚持中国的方式,那我为什么要出来学呢,所以我就想到,把美国的东西学回去,在中国加以改造,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路径。我在美国的三年里,学的就是神经心理学还有药理学,因为要解决临床实际治疗的问题。当时美国精神科方面的材料,哪怕是最基本的内容,我都收集整理起来,最后扛了两大箱子的书回来。别的没有带什么回来,因为人文科学没有什么仪器。
王:您回国后是怎么将在美国所学内容用到工作中的?
李:我回国后,参加了一个精神科的会议,当时好多精神科专家也在琢磨我们中国精神科的走向问题。我回来跟他们一说,他们高兴地让我跟他们一起干。我们国家早先神经、精神科是并在一起的,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以后,我一个神经科大夫成了第一届精神科的全国委员,当然神经科我也是第一届全国委员。有的医生跟我开玩笑,李大夫你是个两栖专家啊。我说,什么两栖专家,神经科和精神科我都马马虎虎,就这么一个人。就这样我把一部分精力转到人文科学上去了。
当时我们医院也有一些专家对人文科学很有兴趣,比如消化内科的柯美云、我们科的魏镜等等。当时我们大概五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每个礼拜四下午碰一次头,把门诊或病房看到的不太好解释的、可能涉及心理方面的病例拿出来讨论。后来,鲁重美书记【14】对这个很有兴趣,也参加了,她说不如成立个科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吧,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心理生理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心理医学科。
一开始成立时鲁重美书记让我当主任,但我当时已经是神经科副主任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当个教授,我就推荐魏镜当,我当个首席专家就行了。魏镜那时候才30多岁,但能力强啊,所以当时就这么定下来了,心理医学科到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王:当时在医院里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李:其实好多人都有心理问题,比如要做胃大部切除手术的病人,他心理上肯定会有顾虑,会想切了以后还能吃饭吗?能吃多少饭?能活多长时间?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心理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就先成立了这么一个专业组,然后组里的成员会经常性接到别的科的会诊申请。碰到心理方面可能有问题的病人,我们就集中精力帮忙解决问题,所以当时很受病人的欢迎。有的病人就说,得病那么多年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通过我们这个组,才明确了。
王:当时国内整体的心理卫生状况是怎样的?
李:当时我们对心理卫生健康是不太重视的,我这个话说得重一点。因为当时一些专门的精神病院,他们的医生、护士都说自己的医院是疯人院,他们自己都没觉得他们是搞医疗、科研工作的人。我刚接触精神科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在看这方面的书,有的人就觉得我看书没用,但我总觉得精神科将来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我们中国的精神科现在跟过去相比而言已经好多了,按我的看法,这还不够,还需要再加油。
王:您在科普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还出版了关于失眠、脑死亡等方面的书籍,您从事科普的初心是什么?
李:我因为看书比较多,也有一些心得体会,就想落笔写一些东西出来。确实写了一些科普文章,大概有200多篇,名义上也被大家定了一个科普专家的称号。那么我最初为什么写科普呢?主要是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的常识了解得太少,或者了解得有点片面,我希望能够通过科普把这种状况纠正过来,出发点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写的科普文章什么主题都有,有的有点科普性质,有的有点好玩儿的性质。我主要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科普文章里面得到一些启发,知道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一些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人能像这个病人一样幸运。某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得了抑郁症,我叫她吃抗抑郁药,她不肯吃,她觉得自己没得抑郁。结果有一次,她假装擦玻璃窗,就从窗户跳了下去,人就没了。我感到特别惋惜,抑郁症欺骗性极大,所以我一直强调,科普很重要,我们国家一定要重视精神科的发展。
王:您在协和工作了几十年,您认为协和精神在您身上最深的烙印是什么?请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李:我认为协和精神应该代代传承下去。我不是什么大大夫,就是一个小医生,在我身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大故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很喜欢看书,我想引用美国一本《西氏内科学》【16】上序言里面的四点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从医以来的一些感悟。
第一点,医学是一门艺术。我刚看到时不理解,怎么医学变成艺术了?后来仔细想了想,确实如此。医学你要深入做的话,真的有点像艺术了,比如医学美容要把一个普通人变漂亮,骨科要把骨折的腿修复好,这不是艺术是什么?后来学医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
第二点,医学是一门科学。这个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医学里面有很多的“X”,代表没有解决的问题,像我们神经科的“X”太多了。我经常说,我们一辈子能解决一个“X”就是大师了。所以这个我不用举更多例子,年轻大夫一看就懂了。
第三点,我觉得更重要了,医生是一个职业。医生是人,要生活,也要吃喝拉撒,也需要挣钱养活家里人。医生不可能像神仙一样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能做到的是尽量去救治。所以不要把医生看成全能的,要多一些体谅。好多人都认为医生就该什么都能看好,这是不对的。
最后一条,一个临床大夫必须要整天陪在病人的床边。这个是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们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在病人最需要你的时候陪在病人的床旁,不管病人还能活多久,作为医生陪在他旁边就是一种慰藉。
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大夫应该做到的几点,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要说什么大医生、小医生,就是做一名合格的医生。这就是我对年轻大夫的一些忠告。
王:您退休以后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李: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只有一个爱好,不是医学,因为医学于我而言纯粹是弯道超车,我最爱好的是历史和考古,所以我书架上除了医学文献以外就是历史书。我觉得历史挺有意思,比如人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能出现什么问题?这些都很有探讨价值。
我其实是85岁才真正退休的,其实还没有多久。85岁以前我都是骑自行车从家到协和上班,再骑回来,后来到了86岁,因为行动不怎么方便了,我就不去了。人家之前都跟我开玩笑,李教授你也是80多岁的老头了,要小心啊。但是上班的时候,跟病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现在闲下来了,就愿意没事儿看看历史书,也觉得很开心。
注释
[1]许英魁(1905-1966年),河北饶阳人,著名临床神经病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中国神经病理学奠基人。
[2]位于大脑半球内侧面的额中央前回区域,为下肢(膝关节以下)、肛门和膀胱括约肌的运动功能区。旁中央小叶病变出现对侧下肢瘫痪及排尿排便功能障碍。
[3]低温治疗是一种医疗技术,通过将身体暴露在非常低的温度下,以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将低温定义为介于-110摄氏度至-160摄氏度之间的温度范围。
[4]施今墨(1881-1969年),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
[5]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始建于1908年,现为市属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暨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等任务。
[6]深感觉是指感受肌肉、肌腱、关节和韧带等深部结构的本体感觉,即肌肉是处于收缩或舒张状态;肌腱和韧带是否被牵拉以及关节是处于屈曲还是伸直的状态等的感觉。
[7]任何动作的准确完成需要在动作的不同阶段担任主动、协同、拮抗及固定作用的肌肉密切协同参与,协调运动障碍造成运动不准确、不流畅以至不能顺利完成时称为共济失调。通常根据病变部位分为小脑性共济失调、感觉性共济失调、前庭性共济失调、大脑性共济失调四种类型。
[8]维生素B12缺乏症是由于维生素B12摄入不足或吸收不良导致的贫血、神经系统和皮肤黏膜受损的营养缺乏性疾病。
[9]也被称为肌萎缩侧索硬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神经性疾病,主要对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以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部肌肉造成损伤。
[10]营养性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又名营养性大细胞性贫血,镜下显示大细胞,正色素。
[11]郎景和,1940年4月18日出生,吉林珲春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科专家。
[12]张振寰,1941年4月21日出生,江苏沭阳人。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外科教授。
[13]利凡诺尔,也称乳酸依沙吖啶、雷夫奴尔,为消毒防腐剂,可用于小面积、轻度外伤创面及感染创面的消毒。
[14]鲁重美,1949年8月13日出生,湖北武昌人。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知名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15]崔丽英,1956年12月27日出生,辽宁沈阳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
[16]《西氏内科学》是由国际著名医学专家共同撰写的一部医学巨著。被誉为“标准内科学参考书”,是广大临床医生和医学院校学生、研究生必备参考用书。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慧康网 » 口述历史 | 李舜伟:跟病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20250911